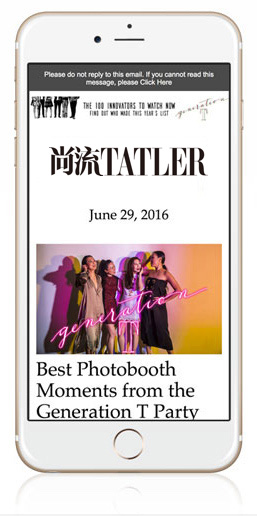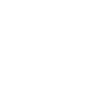2020年春节前,艺术家徐冰为了在芝加哥斯马特美术馆的展览来到了美国,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还会更久。1990年代初,他从北京前往纽约,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往返于中美之间,在两种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和灵感。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让这一代优秀的中国艺术家活跃于世界舞台,也将中国艺术圈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市场化浪潮之中。而现在,一切再次改变,承受着不可抗力因素的世界,正在重新竖起种种壁垒和边界,试图在混乱中构建新秩序,而且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

徐冰位于纽约的工作室原先是百年前颇受欢迎的意大利面包房,室内还保留着半地下的砖石空间和烘焙炉的“遗迹”。在这段不能出门的时间里,徐冰把自己交托给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他甚至搞了个小篮子,不用爬三楼楼梯,就能给从大学来到纽约的女儿和侄女来回送饭;戴着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地接收快递;认真地打扫卫生,做家务,整理小院子。在我们采访开始的半小时前,他还到顶楼上去看了看街上的游行。整个美国的大街小巷似乎都陷入了炙热的叫嚣中,而徐冰这个既是“在场者”又是“旁观者”的人在这些叫嚣之外,生活之中,依旧思考着艺术的事情。
既是病毒,也是良药
用徐冰的话说,现在的自己每天都处在像做版画一样的状态 ,“极其认真”地做着“过去从来不认为值得这么认真去做的事情”。对他来说,之前从没有过把这么多大块大块的时间用在处理家居的琐事上。“这时候对自己有一种陌生感,因为有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是我。其实开始觉得艺术是无力的,没有用。”徐冰说。不仅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采访的艺术家中,有不少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甚至带着巨大的无力感和困惑,同时也有一些人开始强调艺术的治愈力量,但徐冰却不认同“片面的治愈力”。他认为,“好像很难把艺术和疫情这些东西直接地对位起来,或者说它面对这个东西的作用,因为其实艺术的功能分很多层次。”
我们时常反省艺术是什么,经过长久以来的沉淀,人们已经把艺术放到了越来越高的位置上,但是在当下这个“非正常”的世界秩序中⸺呼吸的危机和谣言的泛滥,人们已经渐渐失去了判断的支点⸺人们又越来越不清楚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这段时间里,徐冰忙着做他口中“各种各样不值得做的事情”,可是脑子里却一直没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发现,“其实当代艺术的作用有点像新冠病毒。一类的当代艺术是在过去的文化序列中没有被排序的,它的基因链到底怎么回事根本没搞清楚,像是给人类的文化生态投入了未知病毒,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这时候艺术领域需要判断这个东西是什么,从中整理出新的概念,生产出新的知识。这也是我的工作所追求的。”
艺术家对时代都是敏感的,使他们对旧有的方法论进行改造,同时艺术家也是思想型的人,并且善于把思想转换成艺术的表达语言,这才是重要的部分。因此在徐冰看来,必须用一种有效的艺术语汇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过去被使用过的语言都不值 得再用。从80年代末的无人能读懂的《天书》,到90年代融合东西方文字的《英文方块字》,再到充满新时代标识、人人能解的《地书》……徐冰就像“新病毒”一样,始终挑战着艺术界旧有的“免疫系统”,带来新的冲击。
而艺术本身对他来说,却是一剂良药。“这种疗愈作用并不指向外界,而是完全指向自己的内心。”他说,“在你生命最危急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候,艺术总会出现,有时候可以说是救命的。它确实永远和你站在一起,也是最值得信赖的。”这种信赖并不是对艺术品的信赖,而是对艺术作品诚实性的信赖。正如我们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艺术比任何东西都诚实。即使艺术家本身不诚实,他的作品也会诚实地记录他的不诚实。”徐冰说。
他口中广义上的艺术,包括了文学、音乐、绘画等等在内的多种表现形式,无论外在呈现的结果如何,好的艺术都即使病毒,也是良药。

反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艺术
“现在的世界很悲哀,真的。”徐冰感叹道。
不得不承认,当代艺术某种程度上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被推动和放大的。40年前,星星美展悄悄地在栅栏上“开展”的 时候,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而现在北京和上海遍地的国际性画廊,私立美术馆、几大艺博会、各个城市的双年展,让当代艺术变成了一种不得不追赶的时尚。中国的艺术界在 近2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与国际市场体系的接轨。徐冰以及其同代的艺术家,便是这场中国当代艺术浪潮里的弄潮儿。他们将中国艺术带向世界,同时又在西方的视野下反观中国。

而现在,依赖于全球化推动的当代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讨论‘艺术何为’。但是我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不要说艺术,包括我们的生活、工作方法,整个世界的秩序都会被影响。”当世界宛如一个不受控、失去坐标、混乱转动的魔方,艺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方块时,作为国际性的艺术家,徐冰反思着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它的盲点。

“中国的艺术确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从文革之前,早期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最后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但我们其实发现这里面需要有很多盲点,需要调节。”徐冰说。那么这个“调节”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原来全球艺术系统中没有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在国际上工作的艺术家,徐冰认为,“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特殊经历所积淀下来的东方的哲学智慧、早期的社会主义试验的积累以及与西方文明对冲的经验。这东西作为复杂的基因,藏在你的身体里,最后就会跑出来,面对世界格局的新问题以及时代现场改变,其实它是有效的。”

东方的哲学智慧在徐冰这代人的成长历程中,其实是一个被撕裂的状态。他的青少年时期处在一个“极具实验性的社会大课堂”中,为了某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既无法追溯过往的传统文化,又不明确该往何处而去。因此,徐冰觉得那些中国传统智慧其实是后来“恶补”的,但好在,如他所说“中国文明和文化它有一个特点,是通过言传身教,以一种很细微的方式被传递的,很有韧性。经过这么多劫难,仍然还是这么存在。当然这些特性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种族的某些弱点。”
2018年,UCCA当代艺术中心全面整修后呈现了“徐冰:思想与方法”大展,展览力图全面梳理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40年的创作历程。回想展出的60多件作品,在极具前沿性的同时始终都带着中国文字和文明的痕迹,言传身教的文化氛围便是徐冰获取中国文明中有价值部分的真正来源。他在作品中掌握着一个“度”,什么时候更尖锐,哪里的色彩要含蓄,最终决定这些“尺度”的其实是来自艺术家的身体深处的文化基因。
如果我们从原点回溯徐冰的重要作品,便会发现其中暗藏着的共通点:他非常努力地、认真地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表象事实,但这个事实的本质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不论是创造出一种语言系统的《天书》《英文方块字 》,还是延续至今的《背后的故事》《凤凰》等作品,以及电影《蜻蜓之眼》,无一不在使用这种核心 方法。

艺术是命中注定的
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工作室度过的半年里,除了思考艺术的问题之外,徐冰还重新读了一些年轻时候读过的经典文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对18世纪的人来说,小说是最流行的娱乐,作家就跟现在的流量明星一样,一家人或一群好友在晚饭后围着火炉开始读小说。徐冰发现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些大文豪依旧了不起,“就在于他们所揭示作为自然人最本性的那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原型”,让你对人类文明的流变和人的劣根性的反省有更多的参照”。
不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自己,徐冰总觉得人其实是非常被动的,都是可怜的,没有人能够脱离他所处现实的现场。而大时代往往就像一场泥石流似的,裹挟着沿路滚滚红尘从山上一路向下。“人并不能够实现逆流而上,只能够完成在夹缝中或石头与石头间的自救。”徐冰说。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艺术也不是由自己来计划,它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人的作品,虽然思考来自于社会现场,但艺术家最终完成的是只属于你的闭合的圆环,过去的和后来的作品之间相互发现与相互注释。这个,是艺术最核心的部分。”
在这种宿命感的笼罩下,我们问徐冰是否有感受到“高光时刻”。在如此多的成就面前,他回答“我从来没有高光时刻的感觉”。当然,他也承认在宣布获奖的某一瞬间确实是高兴的、激动的,但转瞬即逝,那些东西最终都没有办法让他真正体会到逃脱出命运的泥石流,而站在山边的高峰。
“其实对我来说,生活中真正可以给我带来愉悦的,就是我可以不受打扰,专心地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完美。有些事情是可以推到无限的。”徐冰说。一张纸、一支笔、一杯咖啡,没有人限制他,没有人左右他,看思想能够推进到哪里“ 。完全在于我自己,谁都赖不了,这个时候做到我认为‘可以’的程度时,我会有一点‘高光时刻’的感觉。”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孤独的理想主义生活,即使背负着强大的宿命感,依旧在寻找自我内心的充盈。徐冰口中的“高光时刻”代表着一种灵魂满足,就好像你找到了一样东西,也许它对全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和作用,而你视若珍宝,追求着它未来无限的美。 现实将我们暂时隔离起来,但在纽约工作室的徐冰,以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依旧在思考更永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