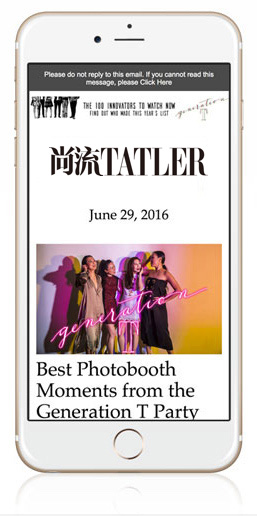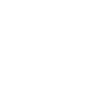这个时代什么都快,会让人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太市场化了。
我们这代人面临一种危险——容易被人带跑,尤其是远离学府之后。
每次回校园我就觉得特别踏实,思考根基的问题让我感觉到一种平衡

黄色针织衫Loro Piana;蓝色休闲裤Louis Vuitton
今年6 月,过完36 岁本命年生日的郎朗,就要结束他人生中最悠长的一段假期。跟几年前在音乐会彩排间隙见面时比,郎朗整个人的状态轻快而放松。身为资深球迷,他称这段时期为艺术生涯里的“中场休息”。
音乐家不孤独
郎朗说,为了保护双手,自己通常是一个人踢球:“对着墙咣咣咣练,是有点闷,但没办法,大多数成年人踢球比较野蛮,踢之前知道这个人是弹琴的大家别铲他,真踢起来就全忘了。我比较担心冲撞,因为一旦有点什么就可能一个礼拜练不了琴,我可是指望着能弹一辈子的,就会特别小心。”
如今,郎朗左手的腱鞘炎已痊愈,他恢复了每天两小时的练琴节奏,为7 月6 日在美国坦格尔伍德音乐节上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的复出首演做准备。回归欧洲舞台的演出是在琉森音乐节,他将与音乐总监里卡尔多· 夏伊携手,而国内则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青岛一个全新开幕的音乐厅。
“我出生在沈阳,9 岁之前一直在那儿生活,但说起来我也算半个青岛人,度假常去即墨泡温泉,每次去完之后浑身就像重新充了电一样。那里重建了一座真正的古城,更有文化底蕴了。”5月,郎朗博物馆& 艺术世界以及郎朗的院子落户即墨古城,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回归,“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小平房、四合院。我想有个安静的地方接待朋友,一起欣赏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办音乐节、音乐体验营,让全世界爱好音乐的孩子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是怎么回事。我去过即墨的民谣节听现场,有很多民族性的作品,没什么商业气息,我很喜欢。”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郎朗参加了一档美食节目,烹饪水平只限做方便面的他一开始有点抗拒,但他想到了年少时曾给他很多激励的一群小伙伴,大家已失联20 多年,能不能通过节目找回来?“我想请他们一起吃顿我妈包的酸菜饺子,我就好这口。原来我连和面都不会,不敢动刀,怕伤手。这回稍微学了点,主要还是负责在旁边捣捣乱。虽然想找的小伙伴们也没全找着,但还是来了不少人,节目录完之后我们就拉了个群,整天聊天。”
教育就是要接地气
说到旧时朋友,彼此相逢如故,郎朗像孩子一样开心全写在脸上,更让他喜形于色的是郎朗音乐基金会最近终于在国内落地了。“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在海外做了10 年,且不论成就如何,至少找到了清晰的方向——只做音乐教育。有的基金会什么都做,很容易做迷糊了。其实音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不太公平的,你花费的苦功未必能带来同等的成绩,需要一些运气和机遇。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所以希望提供一扇大门,给追梦的人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打电话去给孩子们推荐老师也不是不行,但这种做法太原始了,折射力不够,平台和机构的力量就不一样了。既然很多人愿意使劲,我就让他们知道劲往哪儿使才能让人得到真正的进步和体验。”

西装、衬衫、领带均为Stefano Ricci
这些年,郎朗在音乐教育上花费的心力并不亚于音乐会。前不久,盲人钢琴少年刘浩在美国的首场独奏会后特别感谢了郎朗,称他为“心中的太阳”。郎朗说自己第一次见刘浩时他才6 岁:“小男孩特别乖,见到我就扑过来,不管说什么一下子就能领悟,很有灵性。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家大剧院,他跟我一起弹李斯特的《钟》,弹完我就跟其他孩子们说:‘看看人家,看不见都比你们弹得准,还坐在这里干嘛,快练琴去!’” 6 月底,郎朗将在北京丰台区的三所学校开设郎朗音乐教室,而他每周一分钟在线上更新的“微课堂”,也会持续为大众普及古典音乐。
“大多数时候,社交媒体被大家用来娱乐,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我要做的是让大家在知识上受益,不管是直播、抖音,还是知乎这种深度的知识分享平台。很多人会给古典音乐乱扣帽子,这其实不奇怪,就像外国人听中国音乐一样,还是需要普及。我最崇拜的帕瓦罗蒂,在古典音乐方面的建树无人能敌,不管你懂不懂音乐,都能通过他获得享受,他是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第一人,我听他演唱感觉心都被他打开了。我小时候也崇拜霍尔维兹,可惜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所幸的是后来跟的老师是他最厉害的学生。如今高科技的发展让教育变得简单易行,成本也降低了许多。”这几年,郎朗的公众形象似乎越来越亲民,他笑着说,自己的性格其实一直挺接地气的:
“虽然以前给人的感觉像是个工
作狂,但我始终觉得古典音乐不
应该是端着的。我希望以朋友而
不是音乐家的身份去和大家交
流,调整自己的姿态,以一个正
常人的思路去让大家理解音乐。”
对于初学音乐的孩子,郎朗建议从莫扎特、肖邦开始,用卡通和多媒体等有趣的手段启蒙,不要用严肃的大部头吓到孩子。“也不是不能听柴可夫斯基,但可以先接触《胡桃夹子》《天鹅湖》这种有故事性的作品。没有情节和画面感,孩子是接受不了的。国内的音乐教材确实跟不上时代了,感觉还是上个世纪的那一套,我已经着手帮忙改编,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让大家看到改变吧。”
以赤子之心看艺术
采访前,郎朗去了一趟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在四合院里边喝茶边听古琴,这种缓慢与平静,对于曾经的他来说可谓奢侈。“之前平均两天开一场音乐会,很少有机会让自己慢下来,在钢琴演奏之外思考一些音乐作品方面的事。最近我和国内的顶级学府走得很近。今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建校120 周年的庆典上,我有幸成为艺术总团总顾问,想想距离在北大当驻院艺术家已经过去10 多年,也是时候回归校园了。”

西装、西裤、衬衫、领带、口袋巾均为 Stefano Ricci
郎朗谈起大提琴家马友友,眼中流露一丝崇拜:“每年马友友都在哈佛大学做一些纯学术的研究,完全没有商业上的利益关系。这个时代什么都快,让人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太市场化了。我们这代人面临一种危险——容易被人带跑,尤其是远离学府之后,被带跑的可能性也变大了。所以每次回校园,我就觉得特别踏实,思考根基的问题让我感觉到一种平衡。虽然前阵子不让我练琴确实难受,跟没吃饭似的,但回头一想还是尝到了一点甜头,慢节奏让我隔绝了一些东西,也给了我新的营养。”
因为父亲喜欢收藏古董,郎朗也对中国的山水画情有独钟,从范曾到崔如琢,以及他的艺术家好友娘本的唐卡作品。但若说收藏,他手中最多的还是柴可夫斯基、李斯特等音乐大师的信件。“我18 岁生日的时候,有一位收藏家送了我一张柴可夫斯基的签名,特别珍贵。在我看来,艺术是无价的,为了收藏喜欢的作品,即便价格不菲,也要舍得投入。”
郎朗的恩师加里· 格雷夫曼是一位大收藏家。“我在老师的家里看到了很多东亚的艺术品,包括日本、菲律宾的,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他特别热爱东方的文化与艺术。还有德国的克里斯托弗·埃申巴赫,家里也收藏着大量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法国、中国的都有,但感觉特别抽象,我不太懂。可能我喜欢的东西还是比较传统的。”郎朗坦言,除了画家韩美林曾以朋友的身份送过他一些作品,在现当代绘画收藏上他还是一名初学者。因为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郎朗正努力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
5 月底,郎朗出席了首届“艺览北京”的开幕活动,当发现自己最近相当关注的张晓刚也去了现场,他很后悔当时没来得及跟这位艺术家聊一聊。“我一直喜欢逛博物馆,从人类的历史中找感觉,但是对于现代艺术,我虽然能看懂一些,就是喜欢不起来。当然,前阵子在美国刚去了匹兹堡的安迪· 沃霍尔博物馆,感觉还是很震撼的。还有达利,他在我心目中是科幻漫画的鼻祖。”
在郎朗的理解中,艺术不分古今与东西,他希望自己的博物馆可以和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机构共享展品和资源,不仅仅是钢琴和音乐,还可以有绘画、雕塑、手工艺品等等,让更多人在高品质的艺术氛围中受益。
更多封面故事及精彩内容,请详见→→《尚流TATLER》六月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