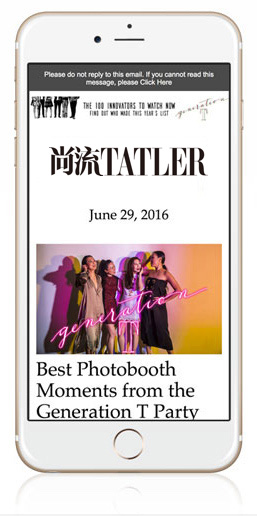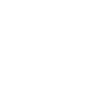见到咏梅的那天天气很好,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套装,头发梳得平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看得出来她的心情不错。事实上,她也确实是一个擅于快乐的人,大到取得一个成就,小到做一桌菜,都能让她感到愉悦。拍摄结束后,咏梅抱着那束用来做道具的梅花回到房间,笑盈盈地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可以带回去插在花瓶里,挺好看的。 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咏梅的标准化生活。作为一个影后,恬淡克制;作为一名演员,端庄温婉。但咏梅却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内在严肃”的人。她选择用当下的生活方式来充实自己的每一天,因为在她那张平静时也充满着某种坚定感的脸庞背后,早已有过了对自己要什么的思考。她笑盈盈地跟这个世界对话,并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坚定地说不。
 咏梅身着 GIADA弹力羊毛套装、 GIADA丝质印花上衣
咏梅身着 GIADA弹力羊毛套装、 GIADA丝质印花上衣
咏梅:平静,愉悦,再多一点相信
Tatler:您最近一直都待在家里吗?这段时间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 咏梅:我最近待在家里,本来有一个电影要在1月份拍,但因为剧本要调整,暂时放到明年了。所以这段时间就变成了轻松自在的纯生活状态,每天吃吃喝喝懒懒散散的,过年的时候在家请客和朋友聚会,很愉悦。
说到去电影院看电影,好久没去了很是想念,春节期间就跑去看了几部,《奇迹》我有参演,所以第一部电影就去看了《奇迹》。去年的拍摄,两个大夜,好多久违了的新鲜感受,当时还发了一条“杀青啦”的微博记录了一下。一方面,是被导演身上饱满的 、自信的和新鲜的创作能量所打动,合作很愉快,并且觉得自己也有很多潜力可以被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和千玺的合作也让我惊讶,这个小朋友有那么大的定力,虽然我和他只有短短一场对手戏,也能感觉到他能够给予角色极大的耐心与尊重。
Tatler:您在拍摄过程或观看过程中受到的触动来源于哪种情感?因为电影在讲小人物的奋斗,同时也基于浓厚的家庭亲情? 咏梅:打动我的是人物和故事本身传递的那种,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家庭亲情间的厚厚的爱。这样的爱是所有向上的动力,战胜困难的勇气,是努力拼搏的信念。
“年轻的时候我 还不懂,觉得好像 一定要玩了命地 做些什么才算成功,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不太适合这种急功 近利的方式。我就会 想,一定要这样才叫成功吗,如果换一种方式走另一条路又会怎样呢,可能会艰难但是更有趣”
 咏梅身着 GIADA香氛蓝丝毛套装、 GIADA白色高跟鞋;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咏梅身着 GIADA香氛蓝丝毛套装、 GIADA白色高跟鞋;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Tatler:您的戏在播的时候,您会去看大家的评论吗?前段时间《风起洛阳》热播,您饰演“圣人”一角,您会有焦虑感还是隐隐的期待感? 咏梅:隐隐的期待感是有,焦虑感是没有的。因为对于比较成熟的演员来说,他在完成了一个角色的时候,心里就大概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响。至于那些评论,我原来是完全不看的(笑),现在有偶像包袱了,会看一点。有些观众的评论我看在眼里也会常常去反思,也会成为琢磨表演跟理解市场需求的参考标准。
Tatler:您是一个常常自我反思的人吗? 咏梅:对的,我是。我觉得一个人要是想开心地活着,反思是很重要的。要多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在哪里,自己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才有可能去解决或扫除那些阻碍你的部分。
Tatler:听起来您很看重“开心地活着”,生活中您是一个很容易自我愉悦的人吗? 咏梅:我很容易自我愉悦,这也是因为40岁以后,人随着长大和成熟,对世界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包括对自我的看法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准则和更开阔的视野。我非常容易通过很小的一件事情感到很开心。像我昨天在家里请客,邀请了几个好朋友,做了几道简单的小菜,其中一道是我家乡的小吃羊肉烧麦,他们吃得美得不得了,每个细胞都在赞美我的厨艺,他们吃得很开心,我看得也很开心。第二天他们还会专门发微信来说,真的是美厨娘啊。我就好有满足感。
Tatler:能够从细小的事情中收获巨大的满足感,是您的能力,也是您的选择。是不是相比较于宏大的事业,甚至人生价值的实现,您更倾向于体验小事带来的愉悦? 咏梅:其实,无论怎样我只是不喜欢功利地活着。只想要找到内心的平静和自在的感觉,在这样的感觉中获得满足,这种满足能在微小的事情上得到也挺有成就感的。年轻的时候我还不懂,觉得好像一定要玩了命地做些什么才算成功,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不太适合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我就会想,一定要这样才叫成功吗,如果换一种方式走另一条路又会怎样呢,可能会艰难但是更有趣,还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和体会,最重要的是不容易被裹挟,可以清醒地做自己。
我现在生活得很自在,很容易开心,也不会轻易地被什么东西裹挟,有时候甚至能够带给别人一些参考经验。当然,我相信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拿了奖之后这几年有了一些光环,但其实在我拿奖之前,我已经认定我自己是成功的,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什么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与幸福感。所以我很感激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
 咏梅身着 GIADA塔夫绸风衣、 GIADA丝质印花上衣、 GIADA鎏金渐变百褶;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咏梅身着 GIADA塔夫绸风衣、 GIADA丝质印花上衣、 GIADA鎏金渐变百褶;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Tatler:您之前说自己是一个很酷的人,但很多人对您的印象都是温柔似水、温婉端庄,这样的评价您是认同的吗? 咏梅:我是一个内心严肃但是愿意对世界温柔以待的人,背后的那部分刚性不被注意到是因为人人都喜欢被温柔以待吧。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法有一些疲倦感,尤其在演员塑造人物方面,老是这个类型的来找你,的确会有一些烦闷,老演优点多的人,就容易这样吧。但是这个标签我觉得也没关系,它在这也拿不掉,我也不会去刻意把它拿掉,我再贴别的标签就好了嘛,多几个标签,就没关系了。
 Tatler:您通过什么来保持自己的节奏,让自己比较“定”,进而维护自己生活的稳固性呢? 咏梅:一方面,不断地向内看,去构建自己稳固的精神世界。我很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足够相信我自己,我也知道自己顶得住;另一方面,向外去建立与他人持久而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对我的影响很大,情感对我的支撑非常重要。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过程当中,经历到困难、苦难的时候,都是这一部分情感给了我力量和依靠。
Tatler:您通过什么来保持自己的节奏,让自己比较“定”,进而维护自己生活的稳固性呢? 咏梅:一方面,不断地向内看,去构建自己稳固的精神世界。我很坚定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足够相信我自己,我也知道自己顶得住;另一方面,向外去建立与他人持久而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对我的影响很大,情感对我的支撑非常重要。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过程当中,经历到困难、苦难的时候,都是这一部分情感给了我力量和依靠。
还有一点是真正的沟通和交流。我最近正好在看一本书,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它是一本谈话类的书,就是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交流方式,它可以是一个人、一个你手头的工作、做一顿好吃的饭菜、大自然或者是一本书……真正高质量的交流是一种能量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梳理甚至净化自我,帮助我们去更新和建立内心的秩序。
“我相信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拿了奖 之后这几年有了 一些光环,但其实在我拿奖之前,我已经认定我自己是成功的,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Tatler:在您看来,亲密关系可以比作什么东西?为什么? 咏梅:我感觉很像跷跷板。这头儿和那头儿,哪个也不能缺,而且必须有互动,你必须得给对方力或者你要配合对方,你才会有游戏感,你才会把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开心。如果有一方不付出或者是无动于衷,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系,更不要提什么亲密感了。
在我的亲密关系里,我是愿意主动付出的那一个。因为爱这个东西不是说只有别人给你,或者天上会掉下来,而是需要你自己去选择爱的给予方式。比方说我对待爱人,因为我的工作常常需要出去拍戏几个月,留他一个人在家,所以我回来之后,一定会努力让这个家是特别温馨的,我要给他所有我能给的温暖,营造幸福感。他付出了耐心、等待和支持,那我一定要回馈以爱的方式。
Tatler:亲密关系的建立与培养,您认为需要我们具备哪些能力? 咏梅: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环境的压力太大,或者大家比较悲观,我观察现在有些小朋友,在情感方面多少都有些顾虑,甚至避而远之,也有一些不知道是成长还是个性的原因形成的脆弱和容易受伤,我理解这背后肯定有复杂的原因……
作为演员,我们是需要观察研究人的,我也希望自己去传递情感或爱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我不能说我就很成功或我说的就是对的,我也有我需要学习的部分,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感情确实是一种充满挑战的存在,它能给你带来安慰的同时,也是拓展你生命宽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是需要你去勇敢和付出的,在这个过程里,也同时塑造了我们生命的丰富度……我挺希望大家更多地去探索和讨论这部分,当然我也不是想改变或否定现在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也会有点儿好奇,未来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
Tatler:您对网络和社交App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咏梅:还是在观察吧,观察并尊重。
最近和朋友也有聊到,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跟网友沟通,实际生活里面对面的交流都很泛泛,有的跟近在身边的人说话也要通过手机,我看到的是,大家渴望交流的同时也有着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我也很好奇这种互联网时代的交流方式,未来在人和人的情感方面带来的改变会是怎样的?我就会在想,是不是年轻的一代人不愿意去相信真情实感的付出会有美好的回报了?这是不是一种逃避?如果是,要逃到哪里去呢?会有怎样的因果?本质上跟教育有多大关系?如果根源是教育不全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去自我教育,那么,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是不是也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获得一些信息,来提升和改变这些局面?
 咏梅身着 GIADA双层羊绒马甲、 GIADA重磅真丝上衣和半裙;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咏梅身着 GIADA双层羊绒马甲、 GIADA重磅真丝上衣和半裙; 佩戴GIADA艺术浸金耳饰
Tatler:明白。我们这次拍摄您和梁鸿老师,分别是在北京和特拉维夫,您对北京的情感是怎样的? 咏梅:我很喜欢北京,我大学的时候在北京读书,当时就想着以后最好是能留下来——这样看跟现在的年轻人来北京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挑战的境况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尤其当你经历了炎热的夏天,秋天突然到来,你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秋高气爽,是北方人喜欢的那种,颜色丰富,色彩明亮,天那么高,抬头看瓦蓝瓦蓝的,心情会很好(笑)。我喜欢在北京的秋天里散步,去公园看叶落,大片大片的树叶落下来,纷纷扬扬的,整个树林里铺满了落下来的叶子,而这在南方几乎是看不见的。
Tatler:这种时刻会让您想起您的家乡吗?正如梁鸿老师的许多作品里都在描写自己的家乡,您对家乡怀有怎样的情感? 咏梅:我和梁鸿老师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她是回到家乡,而我是从家乡出走的。她从小成长的那片土地,人文气息跟我的是截然不同的。你的父母和亲戚朋友,你周围的生长环境,包括你对家乡的哪些东西产生情感,都会从小开始影响你。而我因为小的时候方方面面都不是很快乐,所以对家乡没有像她那么多美好的眷恋。但是家乡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童年的回忆,有亲情的温暖,可能我特殊一点,但家乡对我来说依然是摆脱不了,并且意义非凡的。
Tatler:说起来,您是怎样想到和梁鸿老师共同拍摄这次封面的?您和她是怎样结缘的? 咏梅: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我当时正在做《咏读计划》,梁鸿老师出了一本书《梁庄十年》,这是她第二个十年写的关于梁庄的书了。我读完后,特别感动于她这些非虚构写作的故事。因为其实非虚构写作不讨好,很辛苦,已经很少有人在做了。但她不仅在做,而且她很定,很享受,她写的《梁庄十年》里面,关注的都是家乡最草根的人。你看得到她的灵魂,你看得到她在这本书里面的关怀,同时还有厚重感。而且它是一位女性完成的,这种视角本身就非常独特与宝贵,令我很尊敬。
所以我在《咏读计划》里推荐了这本书,当时我们还说,她下一个十年还要再写“梁庄”,我说如果十年以后她写了,那我十年以后再推她这本书。
Tatler:好的,谢谢您,那也期待我们十年后再来一次思想的碰撞与对谈。
正如咏梅对于“温婉人设”的倦怠,一直被大家称作“乡土作家”的梁鸿,认为这个称呼并不恰当。梁鸿正在特拉维夫长期出差,最近忙于找房子,最喜欢的就是在空闲的时候沿着特拉维夫长长的海岸线散步,或是去家附近的公园吹吹风。
对一个作家来说,自己似乎总是会与作品产生某种绑定,梁鸿也确实如此。多年来,她始终围绕着家乡“梁庄”进行创作,努力发掘出每个普通人身上的故事,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来展现这些真实。她说自己是个倔强的人,而这点倔强源自骨子里的野。
梁鸿:人不循规蹈矩的部分,恰恰是你可能成为自己的那部分
Tatler:您最近在特拉维夫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 梁鸿:刚到特拉维夫时,我看了朋友做制作人的一个戏,《多余的人》,根据冈察洛夫《奥布洛夫莫夫》改编。导演做了点行为艺术,让一些演员在广场上庄重行走,剧场外面有哲学家在演讲,舞蹈演员表演,然后才是戏剧本身。我觉得挺好玩的。特拉维夫的天气特别好,我住的地方离大海很近,有长长的海岸线,宽阔的草地,和散步、跑步的人群,我很喜欢。
 梁鸿身着GIADA Andi风衣、 GIADA印花连衣裙
梁鸿身着GIADA Andi风衣、 GIADA印花连衣裙
Tatler:听起来是自然风光很美的地方,您认为人是需要定期回归自然去汲取养分的吗? 梁鸿:人跟大自然之间是有内在联结的,不管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当人在自然之中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有一种愉悦。比如你听到鸟叫,看到树林,眺望大海,遇到雪景,都会非常非常地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人类天然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人在内心是有一种想要和大自然联结的渴望的。
但这个联结,又并非一定要回到大自然之中。什么叫大自然呢?这是很难界定的。所以我觉得,人和大自然之间的联结可能有多种方式,在城市空间中也可以寻觅到一些角落。比如在特拉维夫,我住的地方楼下就有一个小小的树林,里边有一些古树,腐朽的枝叶,几张长椅,你可以在那感受到一种幽静,早晨起来鸟声不断,窗外城市屋顶绵延起伏,光线在不断变化,那同样是你和自然之间的联结。
 梁鸿身着GIADA 101一号风衣、 GIADA真丝上衣和不对称半裙; 佩戴Octavia金属项链。
梁鸿身着GIADA 101一号风衣、 GIADA真丝上衣和不对称半裙; 佩戴Octavia金属项链。
“我不觉得我是 乡土作家,这个词 太狭窄了。它已经 是一个被泛滥 使用的词语,一个 词语越是不言自明, 越需要思辨,内核 就越苍白,好像我们 现在一说“家园” 就是“乡愁、怀旧”, 其实它是人类的 一种精神状态, 它甚至是人类的 某种渴求”
Tatler:这种生活方式在国内的城市比如北京,是不是也有呢? 梁鸿:当然。有一次我姐姐从县城来北京,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几天后,她就发现大约距离我家三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小型城市公园,非常粗糙,但里面有小路、古树、草地,还有很多野菜。许多老人去那里抖空竹、挖野菜、散步。后来我和她一起去,看到有射箭的、击剑的,其中一个人在公园里搭了一个特别小的塑料房子,透明的,我姐姐说这人每天都在,在房子里面吹笛子,从早吹到晚。
我简直觉得这地方太神秘了。这个人在家里面也许是没办法吹的,但是在树林里,他给自己建造一个房屋,吹得旁若无人。这就是自然空间提供给我们抒发内在的地方。人类特别能够找到一种跟自我与自然联结的方式。可能城市生活会让你觉得很枯燥,但有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我当时的反应是,天呐,我在这儿住了四五年都没有发现,可我姐姐刚来就发现了。
 梁鸿身着 GIADA丝毛廓形风衣
梁鸿身着 GIADA丝毛廓形风衣
Tatler:跟北京相比,特拉维夫的城市气质是怎样的?它们有什么不同吗? 梁鸿:我觉得北京和特拉维夫的气质完全不一样。特拉维夫更像是国内二三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人们朴素放松,生活得自在随性。当然这也会变成缺点,比如我去办银行卡,一个月了都没有下来,在北京可能几分钟就好了。但是这里的人就算没有拿到银行卡,好像也没有多不高兴,他们对速度没那么在意。
以色列从周五傍晚开始到周六是家庭日,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会关门,你买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要为家庭聚会准备食材,周四周五就要出门去购物。我特意在周六去购物中心看,都大门紧闭,萧条无比。这也很让人不可思议,在中国,周六周日不正是会客、出去逛街吃饭的最好时间吗?以色列人也太不会做生意了。但转念又一想,太好了。它以一种近乎制度和文化的方式培养人对家庭的关注。
Tatler:去年您参与拍摄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可以谈谈拍这部电影的契机吗? 梁鸿:当时在吕梁文学季之前,贾导的工作人员联系我说有一个拍摄,我不知道是拍电影,在那之前也没见过贾导,但他的电影我都看过,我的书他也都看过。我觉得贾导是一个非常专注和沉浸的人,他前期工作准备得非常好,对采访者有很深入的了解,所以一下子就能直戳要害,而且还可以发掘一些你自己可能想不到、平时也不会去说的东西。
后来这部电影我完整地看过两次,很受震动,因为我觉得贾樟柯导演特别擅长和专注于对普通人面孔的捕捉和呈现。当一张普通人的脸在银幕上呈现的时候,他突然间具有了某种意义,不管是美的意义,还是某种象征意义——他都拥有了一种存在感。像我写作也是写普通人,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所以我知道,让一个普通人在一瞬间呈现出美与本质,让他拥有历史感,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画面,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许这个人自己没有看到,但没关系,他就在历史之中;也许他看到了,他会感受到那一刹那人存在的永恒。
“可能我们不能够全部按照自己的 想法生活,但在某一部分,我们要 尽可能地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生活。 我觉得人不循规蹈矩那一部分,恰恰 就是你可能成为你自己的那部分”
 梁鸿身着 GIADA Andi风衣
梁鸿身着 GIADA Andi风衣
Tatler:您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家乡“梁庄”,因为外界对您的标签是乡土作家,您认同这个称号吗? 梁鸿:我倒不觉得我是乡土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经验的某一部分,然后由此你把它转化成写作的素材,和思想的起点。因为我出生于乡村,又在乡村长大,所以它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不管后来是读了硕士、博士,还是写论文,它一定会是你思考的某种来源。
至于将来写作写不写乡土,或者一定要一生写乡土,我觉得是非常次要的事情。因为思想的转化是无处不在的。它不单单是你写乡村才有这种思想,而是灌注到你生命和思考的内部。即使我现在在以色列,我关注的仍然是普通人,他们也许不是梁庄人,但可能是以色列的“梁庄人”。他们怎样去思考,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民族,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生活扑面而来,它不是说你通过这个来思考什么,而是它本身就是你思考的对象。
另外,我觉得“乡土作家”这个词太狭窄了。它已经是一个被泛滥使用的词语,一个词语越是不言自明,越需要思辨,内核就越苍白,好像我们现在一说“家园”就是“乡愁、怀旧”,其实它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甚至是人类的某种渴求。从普通层面来说,它决定了你在哪儿生活;从精神层面来说,它可能决定了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思想,你的艺术形式,你的音乐形式。我们现在真的把“家园”窄化了,也泛化了。
 梁鸿身着 GIADA Andi风衣
梁鸿身着 GIADA Andi风衣
Tatler:此次封面人物除了您还有咏梅老师,您对她有哪些了解?您看过她的电影吗? 梁鸿:我看过她拍的《地久天长》,也看过她拍的电视剧。我很喜欢她,因为我觉得她眼神里有倔强的色彩(笑)。感觉她不是那种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去媚俗的人,她有自己的倔强在。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的倔强在于我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虽然是个高校老师,好好写论文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是想写家乡,就去做了,骨子里还有一点野在里面。
可能我们不能够全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但在某一部分,我们要尽可能地去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生活。倔强,就是不屈服,它是一个能让你拥有自己一点点核心的起点。我觉得人不循规蹈矩那一部分,恰恰就是你可能成为你自己的那部分。
 梁鸿身着 GIADA丝毛廓形风衣
梁鸿身着 GIADA丝毛廓形风衣
Tatler:作为女性作家,您对当下环境中女性的生存困境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女性的生存环境一直非常严苛,不只是现在。从表面看,现在好像女性解放了,也有工作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从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来看,会发现女性的生活环境一直非常严苛。为什么这几年出现这么多事件,其实之前也是有的,只不过这几年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变得更加敏感了。这才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自我提醒作为一个女性,你的幸福并非是一个单独的幸福,你的不幸也并非是单独的不幸。它是女性共同的幸福和不幸。
比如说丰县的那个事件,实际上背后是女性生存的共同艰难。我看到就在想,几乎每个女孩子都是“幸存者”。因为我们在懵懵懂懂的时期,几乎都受过类似的骚扰。我记得我当年有一次晚上学习,外面下着大雨,有一个人在后面跟着我走,当时我也是不懂的。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他是个好人,但是也许他就是个坏人。
还有像我在《梁庄十年》里写的,女孩子从一个村庄嫁到另外一个村庄,立刻就变成某某嫂子,你就没有自己的名字了。在城市里面,你会变成什么太太。这种东西看起来非常日常,但其实里面蕴藏着我们的习俗和观念,这是需要改变和警惕的。这一条路要走很久,某一个新闻事件也许解决了,这个女孩子的铁链可能被摘除了,但是无形的铁链它太多太多,也太久太久了。
Tatler:最后,您理想的人存在的状态是怎样的?或者说您认为,人存在在这个世界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生长? 梁鸿:我现在就坐在特拉维夫的朋友家的客厅里面,面对窗外,和你聊天。窗外是一些大树,再往远处是荒野。刚好起风了,相当于咱们那边深秋的天气,特别的舒服。我就在想,一棵树,它一直在,不管你看没看它,它都在。风吹树摇、春夏秋冬,它是一个非常自在、宠辱不惊的状态。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是这样的状态。一方面我一直都在,不管多少严寒,不管有没有人在看,我都在;另一方面,我要保持一种自在,达成自我的完成与精神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