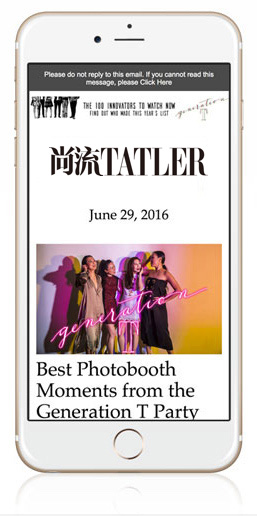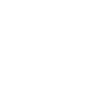刘香成: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讲述故事

953年,我从出生地香港回到母亲的老家福州,在那里读了小 学。当时成绩表里有一项叫“政治表现”,“除四害”和每周的劳动都包含在里面。那所小学是当地的重点学校,班上都是部队家庭的孩子,而我母亲家祖上是清朝文官,后来的“土改”中,我家不算是靠土地收租的,所以被列为“和平地主”。记得“除四害”我去打苍蝇,打得比谁都多,把它们装在火柴盒里交给老师,我也很努力地去捡修枕木的石子,但我永远都是末尾的分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红领巾。那时没有人告诉我原因。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的第一堂政治课⸺身份危机。在“求同”的孩提时代,我对自己的身份始终有个问号在,一直以来我都想要把这件事搞明白,恰恰是由于这一点,这是我对“中国的兴趣”的起点。
而我的父亲1949年来到了香港,是一名老报人。在少年时代,我对新闻的接触和了解,多多少少是跟着父亲和他身边的老先生们学来的。暑假里,父亲就让我翻译美联社、路透社的稿子,我也跑到报社里面去打乒乓球。我是闻着报纸的油墨味长大的, 对新闻的兴趣在我的DNA里。但我却没有学新闻学。去美国读大学前,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在劝我,学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学新闻,因为新闻是没法教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中国,读了政治学。可是我对新闻的兴趣、对中国问题的好奇和探寻都深埋在心里,一直吸引着我。
当我接触了摄影之后,越发地感受到这种好奇心的重要性。在《生活》杂志做助手的那一年里,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28层的走廊上,我经常看到一些像布列松这样的大人物,那个年代的《生活》群星闪耀,大师云集。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对知识、对人的高度好奇。所以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很难去做摄影或是记者的工作。
1978年,就传出了中美要建交的消息,我跟7个美国记者一起作为第一批来北京常驻的记者,其中三个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弟子。离开多年,在我们的记忆里有个遥远的中国,和那个带着“身份问题”的童年混杂在一起。彼时,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件事情不让我感到好奇。我有幸结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文化人,艾青、沈从文、吴祖光、侯宝林……还记得我30岁生日那天,他们都到我家来吃饭,侯宝林先生教我怎么吃螃蟹,然后吴祖光先生又说,按惯例你把螃蟹脚全部吃完后就要做出一首诗来。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中国文人的境界。不仅仅 是在当年的北京,我从事新闻摄影记者的20多年里,我喜欢和文字记者、文字工作者在一起,你会听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他们怎么看中国,西方怎么看中国,然后这些东西会进入我的镜头里,对我产生各种各样的启发,通过阅读和聆听补足我的画面。
我在中国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后,他们派我去洛杉矶两年,熟悉美国报纸的工作。那两年里,我并不觉得满足。全加州的摄影记者都觉得我很奇怪,这里是美国摄影师都想来工作的地方⸺阳光、沙滩,一天完成一个采访就下班了。可是,我要挑战我自己。我要让美国最大的主流媒体看到在没有语言优势的情况下,我还能表现什么;我要让他们放心,我就要自愿去最艰难的地方。
1980年,韩国光州,光州民主化运动;1984年,印度总理甘地遇刺;1987年,阿富汗,苏联撤军;1989年,中国北京;1991年,立陶宛,血腥的星期日;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苏联解体;还有印度锡克族和印度族不断的纷争,伊斯兰卡长达25年的内战……这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也是我作为新闻摄影记者无悔追寻的20年。
常有人问我,这些年里最难忘的画面是什么。我真的难以回答,因为身处在重大的历史和新闻事件的那一刻,它不是难忘或触动而已。 1954年牺牲在越南的罗伯特· 卡帕曾说,“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曾面对着1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苏联坦克阵地,远远超出预料的兵力集结在喀布尔,又向北撤退。塔利班分子都是嗑了药,躲在周围的山头上,扛着火箭炮就朝苏联的军队冲锋。直到我回到酒店厕所冲洗胶卷的时候才反应过来,那个火箭炮歪一点,拍这张照片的我就没了。也是在阿富汗,游击队朝我们的大巴车开枪,子弹穿过座椅射中了我身边的法国记者的屁股,只差不到一厘米就打中了他的生殖器。而在开枪前,我幸运地刚刚跟他调过座位,否则按身材来讲,我的伤肯定更重。那个年代在印度,喝水都可能会中毒;整个阿富汗只 有3条电话线,还没有水,怎么洗照片?韩国光州的学生们自制的燃烧弹每天都在乱飞;立陶宛的革命者也遭到了坦克的碾压。所以,哪件事让我印象最深呢?每一次都是此生难忘的啊。
后来,我决定离开一线摄影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情感已经被透支了。这并不是一份机械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必须要带着一颗真心进入场景,进入故事。也许我不认识他们,但我要找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并且产生一种互动,做到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
回想起摄影最初带给我的震撼,那是1969或1970年,我刚到美国,我走进了在纽约第五大道和90街交会路口的ICP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看到里面的展览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摄影有这样的力量。这短暂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我,因此,在2014年,上海徐汇区的领导要把现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原场地借给我时,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能不能把这里变成中国的ICP。一直以来,中国给了我很多,我 可以给她什么呢?如果有些年轻人像我当年一样,能够领略到摄影的力量,这有莫大的意义。
我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工作与以往的都不同,比我想象中要累得多。这期间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我有幸成为最后一批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的确是赶上了最后的那个时代,在时代的转变中,确实会有很多类型的工作被淘汰,但是摄影师不会。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在讲述故事,图片出现的平台变了,但是好照片的标准不会变,现在人人都可以拍摄,每年会产生7万多 亿张照片,但是最终有多少会进入美术馆?当一个人接触摄影之后,他才会发现好的摄影有多难。形式变了,但事情的本质没变。
摄影是光的艺术,作为摄影师,我始终在追寻着光,研究着光。我相信,人不论是在哪里,舞台上、镜头后、琴键前,都在追找的自己的那束追光,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陈萨•钢琴家
成为言之有物的艺术家
钢琴家陈萨有些日子没从媒体那儿听到与比赛有关的提问了。就算有些什么文章或报道,提到的也是她作为评委的角色⸺今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她就是评委之一。由于疫情的影响,综合聚集性、比赛质量、选手状态等因素,比赛被延期了一年。陈萨对推迟表示理解和尊重,还发文提到了自己的经历,“到华沙参 加肖赛前准备了大约6个月时间,后来仍是觉得可以更充分。”
当评委偶尔会唤起她的回忆。听到过自己曾经演奏过的曲目时,还有“(遇到)我非常喜欢的演奏的时候⸺当演奏的本身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这时你几乎是会非常期待地,并也很自然地跟随着那个人的状态去经历台上的演奏过程。”陈萨对 Tatler说,“这自然也会让我想起以前在自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的状态。”肖赛在波兰国家爱乐厅举办,选手离开了后台的休息区域之后,需要攀上一个陡而窄的楼梯,才走上舞台,“在等待选手登场之前你会记起来,好像在等待出场的那个人也似曾相识,其实是很相似的。”
参加比赛、竞演,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事。 2000年,正在读书的陈萨一个人从伦敦前往华沙参加第14届的 肖赛,获得第四名,在那之后,很多演出商找上门来,要她演奏肖邦。“一段时间之后,我意识到需要‘离开’肖邦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就只演出这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我本能地需要拓宽曲目来满足自己的天性里巨大的好奇心。”
肖赛之后,即便还没有从学校结业,陈萨已经开始受邀巡回演出,正如今日的陈萨工作室在其公号上的介绍,「利兹、肖邦、范 · 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中的出色亮相和斩获佳绩已为她打开了国际演奏生涯的道路」,“一点没错”,陈萨说, “获奖之后你差不多知道音乐市场的一扇门已经打开了,也一直是看得见那个门的。但是那个时间段,我自己也的确经历过一小段低迷状态的时间。”
在伦敦的学业到了告一段落的时候,她不能完全确定要不要当职业演奏家,生活上似乎也碰到了些困惑。“当时觉得生活中是缺乏动力感的,也不怎么知道或者去想明天会发生什么,怎么来迈出下一步。” 陈萨的第一任老师、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但昭义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有没有想过,下一步干什么? “这个问题就像敲钟一样的把我敲醒了,像一个很大的齿轮一样,你看到它咔嚓一下开始转动了起来。”
但老师建议她再去参加一个比赛,这相当于是设立了一个短期的目标,以此来调节自己的状态。“看一下自己到底能有多好、能到哪里,这个念头是一个比比赛更大的内在动力。陈萨带着对 自身潜力的好奇走进范· 克莱本大赛,国际四大顶尖钢琴赛事之一。外在结果不再重要(她最终摘得克莱本水晶大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作为选手参与竞演。
比赛为她打开了职业演奏的道路,甚至成为她从低谷攀出的绳索,陈萨说,“(比赛)在我的生命中应该算是一些里程碑,它串起来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些里程碑慢慢的变沉。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演出还是媒体活动,过往比赛中的头衔和名次都要跟在陈萨的名字后面。“我觉得我们从事或正在学习的内容是丰富得多的,奖牌……我甚至有时觉得挂着奖牌作标签的形式是有一点被小侮辱的,呵呵。”每一次标签扑面而来的时候,她都本能地有些抵触,直到如今。“是的,我曾经有那种类似不可忍受的感觉,你问我怎么应对的,其实我没有应对什么,因为也没有办法。它始终还在那里,其实是一个个体回避不开的。”
匈牙利作曲家贝拉· 巴托克说,“比赛是为马准备的,而不是艺术家。 ”陈萨表示同意, “对啊,我们不是带着挂牌每天生活的。”
2005年克莱本大赛之后,陈萨花了两年时间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2015年,陈萨成立个人工作室。她带着肖邦的43首玛祖卡舞曲走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算上返场时带来的一支夜曲,整场演出持续了三个小时,近乎马拉松。玛祖卡舞曲中,每一首都是作曲家独立写就,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接受北京晨报时陈萨说,“我就想到可以不按照作品编号顺序,打乱,重新找出几组能够形成逻辑关系的组合,有的是从调性上的组合,有的是从风格上的组合,有些是考虑观众的注意力的,比如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大家比较疲劳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些经常被人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旋律性、戏剧性比较强的几首,这样能更好的地调试我本人和听众的聆听体验。”

“一个诠释者是需要尊重原作的,”陈萨对Tatler说,“先要去理解这个作曲家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设法让自己进入这个人的相似维度里。之后用自己去跟作品的个性和灵魂相融合,这是一个我中有你的过程。”
这样一套曲目并不是常规的、侧重商业考量的选项。陈萨能够设计更具艺术性的曲目组合,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主动性回到了她手上。“我觉得空间很大,的确在实践和操作上的形式上是很不同的,对于你任性的空间也是极大的解放。也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只要想到的,其实就可以试试做。”她还尝试了一 些跨界合作。2017年,由工作室独立发行的《德彪西24首前奏曲》,携手如恩设计研究室来完成了专辑所有的视觉设计。专辑在德国录制,陈萨工作室的微博曾发布一篇录制过程中的手记,她写道,「我的感受有些像做实验。有些东西不断重复,而每次听起来都不一样。慢慢发现中间有一些联系……就像一个画板,调色和层次。我发现Debussy也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作曲家!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好像是能够跟着他的思路走进很多不同的空间,看见他的幻想。尽管他从来没有到过东方,但是能够通过像是一些明信片、一些瓷器,以及非常有东方神秘的时间感的东西投射出他在脑海里勾勒的影像。有的也极其有象征意味,脑里会浮现出的达利的画也不为过。」
“还是想回归到演奏状态里,”陈萨说。摘下比赛的奖牌之后,过往的标签时不时还会冒出来,她依然会报以浅笑,“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的世界其实只是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而已。”现在她在往更高的地方行进,成为艺术家⸺这不是某一个时刻下的决定,而是逐渐确定的。或许是年纪渐长,意义对她而言越来越重要:自己的演奏给这个世界、这个作品,以及听的人,到底带来了什么。“其实真正好的艺术⸺包括音乐在内⸺一定是一种多维度的高度融合,是需要修炼的。如果我们是演奏家,那演奏出来的作品就要言之有物。这是很重要的。”
“慢慢的你会意识到,做艺术或许是更有意义的本身,”陈萨停顿片刻接着说,“ta比其他的事更让你觉得踏实、充实,以及不可比拟的成就感。”
叶谦• 导演、设计师
不止于设计

叶谦在2015年专门去了一次曼谷,到寺庙里求了一根签。上面是一首七言诗,诗里面提到“声”“光”“电”,这是三个组成电影视听语言最重要的元素。回国后,叶谦马上报名,从时装设计师,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进修班的学生。
叶谦在服装设计这条路上,算是走得顺遂。他有自己的个人品牌YES BY YESIR,有女装有男装,整个公司在良好地运转着。创立品牌之前,叶谦拿着奖学金入读ESMOD北京,原因是2008年时他参加上海SMG主办的一档设计真人秀节目,拿到了亚军。尽管有这些顺遂的经历,刚毕业没多久的时候,叶谦却有过不再当设计师的念头。“当时是因为没有办法,你要吃饭,你要交房租,你要思考更直接的问题。”叶谦说“,你的一技之长就是它,所以就在当时的时候,那好吧,只有把它当成一个糊口工具。”
“设计只是我的一种谋生手段”,“在商人和艺术家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他在很多个媒体采访里都给了同一个答案:糊口。实际上回去看叶谦在设计上下的功夫,远远超出了 “糊口”两个字。他不断运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解构手法,提出 了轻礼服的概念。在2011年的“少女妈祖林默娘”系列里,用少女这一注脚去解读闽南文化中重要的女神妈祖。在最新一季的FACE系列中,用高度抽象化了的人脸作为主要元素。“你自己身上还是有非常强的作者的心理,表达的特点,所以即使是糊口的一个工具,你也希望可以赋予它一些表达的色彩。”叶谦说。

服装设计能提供的表达空间始终是有限的。“讲一个对设计师来讲非常泼冷水的话,时装设计它又是什么?它不过就是一件衣服,你怎么把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想法概念融入进去,甚至让一些欣赏你的人穿上这样的衣服,同时去把你的观点,往更大的一个层面去突出。”叶谦说。
而电影不一样,它是一种更容易被读懂和吸收的语言。去电影学院之前,叶谦踌躇了一下,“那段时间其实是在动摇,因为人只有在摇摆不定的时候才会有求于神明,其实你内心已经有决定,但是你要的不过是它给你的一个论证这样子。”做林默娘系列之前,他也犹豫过。当时叶谦打电话给外婆,问她自己该不该做这样一个系列。外婆说,为什么来问我,应该去问妈祖。于是叶谦跑去庙里,也是求签,求一个回答。

于是,叶谦特地跑了一趟泰国,求到了那支签,“刚好那个就论证了。”
在电影学院,叶谦完成了自己首部长片《蕃薯浇米》的剧本,只有三十八场戏⸺他对长片应该有什么样的剧本结构并没有概念。但这个置于闽南文化下,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故事,在李少红发起的青葱计划里,从六百多个青年导演的项目中被选出来。选择时候是盲选,单纯看故事,后来匹配上导演履历的时候,审稿的老师们紧张了起来。叶谦从来没有拍过东西,没有短片经验,品牌的视频一直都是外包,最多是自己拿手机拍一拍。叶谦需要瓦解他们的担心。他把整个电影的分镜头自己画了一遍,这个东西说服力很强,“我不用解释,他们自己看里面的剧本,再翻开导演手绘的每一个镜头。那个东西就说服了。”

或许对于青葱的参审老师而言,闽南文化是陌生的,需要更明确的注解。但对于叶谦,剧本里的每个人物,每个场景,都能在他自己的成长里找到原型。归亚蕾饰演的林秀妹,是叶谦奶奶和外婆等人的性格融合。影片中出现的服装,都是当地服装店里能找到的,当地人会穿的衣服。电影出来后,叶谦家里的老人看了,只觉得这是日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没什么好拍的。
实际上留存在泉州的闽南村落本身,已经是值得呈现的东西。片中,青娥(杨贵媚饰)的突然离世给秀妹(归亚蕾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青娥曾经参加过腰鼓队,于是她也要试一试。秀妹从寺庙里找到青娥留下的腰鼓。排练时,她拿着一根用筷子绑成的鼓槌,格外手忙脚乱。腰鼓队的人不愿意好好教她,试了两次,只把她赶到边上,让她一旁练去。几乎是毫不意外地,表演时秀妹摔倒了,眼前一片晕眩。缓过来时她坐在山头上,嘬着酒,目光投向远处水边伫立着的,巨大的风力发电机。

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下,老人与农村被不断推到更边缘的地带“。这个节奏里面,要是有一部分人,不怎么会上网,不太会网络,更没有这些社交软件,甚至他们的这些情绪的表达或宣泄,都没有对象可以去聊,你会发现,那就像是这整个时代的某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一个背过去的阴影。”
一份关于一个族群的、一种文化的情感关怀,服装很难承载了。做完电影之后,叶谦觉得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了一个更整体、宏观的把控。“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传递什么样的理念,要自己想的很明确,如果你的表达并非是取悦大众向的,你对世界的看法并非单一表面化的。从时装设计跨界到电影领域的这个经历,就是我真正的思维方式转变的开始。”

朱洁静•舞者
追光灯下,残酷的优雅
2020年春节,作为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朱洁静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领舞《晨光曲》的表演。从6岁学习舞蹈,9岁独自来到上海求学,20多年的舞蹈生涯里,朱洁静也在改变着,成熟着。
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登台的经历,18岁的朱洁静第一次出演女主角⸺《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她说,自己紧张到没有办法跳舞,双脚站在舞台上,感到整个舞台都在摇晃,脸红到了耳根,独舞的音乐响起,只有一束追光打在身上。她的心理承受力就是这么一点点被磨砺出来的。那个稚嫩的“虞姬”是朱洁静不满意的, 现在她甚至根本不敢去看当时的录像。过了17年,直到今天,她还是怀着感恩又抱歉的心情⸺“很感谢所有的机遇,所有的缘分,也谢谢所有的观众能够包容那么不好的女主角”。在收获了认可和荣誉之后,朱洁静仍旧觉得,当下的自己永远是不完美的,最美好的始终在未来。乐观、坚韧、充满野心和活力的舞者,是她给自己最简单的定义。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论是对舞蹈艺术的认识也好,还是对于跳舞这件事本身,朱洁静也都在做减法,变得纯粹。“我觉得对某种东西返璞归真或者化繁为简。”曾经,很多人小时候接触、学习舞蹈大都是因为它美丽、迷人、优雅,朱洁静也是如此。但现实中真正坚持下来,与舞蹈朝夕相伴的人都知道,它是残酷的。在“天鹅女神”“芭蕾皇后”这类桂冠的背后是变形的双脚、几十年如一日的练功、素面朝天、大汗淋漓……因此,曾经的朱洁静很想要极力地在台上证明她的努力、优秀和美丽,“想要的东西特别多,但当你脱下那些想去证明自己美丽的外壳之后,内心才会获得真正的平静。”朱洁静说。现在的她却更加希望,人们不仅只是记住了她的美,也记住了她塑造的角色,能够感受到一个外表瘦弱的舞者身上所拥有的巨大的能量,甚至“因为我的舞蹈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支持中国原创舞剧,这件事的本身,比我是谁,我以及的名字更重要”。
面对这份残酷的艺术,6岁起学习舞蹈的朱洁静从没想过放弃。在她看来,这不是逼出来的,对于舞蹈的灵性和领悟力仿佛嵌在她的骨头里,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一种天生的宿命感。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某件事而来,不论失败也好,困难也好,都无法构成放弃的理由。舞蹈之于朱洁静便是如此。“我觉得它像是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你的心里,也许你不知道是谁埋下了这颗种子,什么时候埋下的,但是我觉得,但凡在每个行业里能够走到最后的,或者说能够坚持下来的,那颗种子要埋得够深,最后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和热爱才能够发芽长成。”

2008年,从来没想放弃过的朱洁静跌入了一股灰色的低潮里,那是她学习舞蹈以来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伤痛,半年的时间她都无法登台。她被迫躺在床上休养,每天都渴望着走进练功房, “没有舞台,我就不是我,我找不到自己”。整个恢复的过程并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是特别乐观的,以为很快就会康复重回舞台,但是慢慢地她的信心逐渐被现实打垮。经过3个月之后,脱下石膏的她依旧无法走路,同时身边的竞争对手正在把自己的位置顶替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包围着她。这段时间既是她人生最艰难的坎,也是她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朱洁静认真地思考着,自己到底要继续前进还是就此退缩。“就好像你面对悬崖,是‘聪明地’掉头,还是想尽办法越过去。”眼看着有些人就此‘掉头’放弃,去做老师,或者选择嫁人,“这些都能够让生活继续下去,甚至活得比作一个舞蹈演员更好”。但是,那一刻,在朱洁静的心里有一束光,仿佛就是舞台上聚焦在女主角身上的那道追光灯,它在焦虑中忽明忽暗,“但它始终在我心里亮起”。最终朱洁静选择了更难的选项⸺她想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到底能不能飞越人生里最深的一道悬崖。如今,她谈起这段经历,眼里闪着异常明亮的神色。

现在,备受欢迎的原创舞剧《朱鹮》已经演了近300场,在台上为舞蹈奋斗了这么多年的朱洁静感到欣慰和感动的是,中国舞蹈的观众正在转变,或者说观众也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中国舞蹈的新时代。“一直以来,是我们小看了观众,总是片面地认为大众不爱看舞蹈,或者也看不懂。但是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认知出了偏差。”朱洁静感叹道。今天的中国观众,他们对于文化和艺术的品位与追求是超乎朱洁静想象的。每次演出结束后,朱洁静可以跟观众聊角色,一些深刻的看法层出不穷,这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画面。
面对不同与往日的舞蹈热情和活跃的剧场文化,朱洁静也在改变。舞蹈演员虽然注定不会像流量明星一样集万千宠爱,它依旧是美丽与残酷并存的寂寞的艺术,但现在,她明白台下的观众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真心,回到练功房里流汗的自己也就不再孤独。
“台前台后,一种双重的生活在充斥着我的整个艺术人生,我觉得一旦认定了这一点,未来一点都不害怕,我可能就是这条路上的追光者。”

蒲英玮•艺术家
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艺术地反抗
2020年5月22日16:00,蒲英玮的个人项目“时间,历史,我们(为何而战?)”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但在这场开幕式上你找不到艺术家的身影。因为此刻的蒲英玮正在北京画廊周“新势力”单元的开幕派对上进行表演⸺“一个世界,以及我们”。在活动现场,蒲英玮身披旗帜,穿着贴满各国国旗的军用马甲慢速演唱了一首如今代表世界援助主义精神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 其作品《崇高生活月刊》也在此单元参展。第二天,蒲英玮又以“母语:同质浮游”为题参加了“This is Me !中国年轻艺术从业者系列行为讲座。在行为表演中,他分别模仿了小孩与成年人的嗓音去演唱不同语言的歌曲,意在着重于有关身份和历史的阐释。在几个月的沉寂和不安之后,北京画廊周的重启为艺术圈带来了久违的活力,艺术家蒲英玮在这场难得热闹的盛事中备受瞩目。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在其作品内容所面向的问题中看到蛛丝马迹。那些我们日常所忽视的、遗忘的甚或无意识的问题,因一场突如起来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集中且强力地摆在所有人面前,而这些却是蒲英玮一直以来都在关切的。

展览“时间,历史,我们(为何而战?)”在蜂巢当代艺术中的B、C两个厅共同呈现。短暂地穿过一段走廊,视野变得开阔、明亮, 半面残破的墙壁矗立其中,几张大尺幅的绘画作品分别挂在不同的墙面之上,形成一种向外的,宣言似的宏大的空间氛围。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五幅与展览同名的绘画作品,每张画都指涉着艺术家所认为的中国之于世界的问题,或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如,《渔樵问答,人民在冷战市场上购买军火》指向近年来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动荡之后,红色模式将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回应着疫情期间各国对人民管控力度的加强;《分而治之,隔离成为国家主义最后的遮羞布》思考着同样因疫情导致各国边界封锁的问题;《地粮热土,国土资源成为友谊与和平的使者》以中非两国两家国家级媒体共同创办的《ChinAfrica》杂志展开创作,然而杂志名称的字母形态又设计成Cocacola商标的经典形式,其中复杂、隐匿的问题不言而喻。这一系列的作品都共同使用了艺术家所创造的,结合了结合了中文方块字、英文文法以及苏俄文字字体的主要元素与符号的“革命现实主义字体”。蒲英玮认为传统的本土文化(中文)、全球化的语境(英文)与前社会主义遗产的影响(俄文)彼此之间相互糅合、转化代表了当下中国的境况,它像一个横切面一样展现了目前复杂、多元、综合的中国。
从C厅到B厅,如同穿过了一道门走进了艺术家个体性、私密性的内在世界。坍塌在地的半堵墙、赤裸的栏杆上破碎的板面和铁丝网、照映在墙面没有任何停熄意向的热火、凌乱的涂鸦,与C厅明亮强势的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作品所关注的社会环境下的个人。作品《访谈录》(2015)是与在卫生监督所工作的父亲关于独生子和性别鉴定问题的一段对话;《学粤语歌》(2020)回应着不远的当下的问题;《被子弹击穿手掌的回忆》(2020)强调身体感知的状况……同时,以“革命现实主义字体”创作的小幅作品随机挂在墙面与围栏上,是一种布展逻辑和内在主题的呼应,更是一种个人在自我空间和公共关系之间的来回滑动展现,书写着宏观与微观两种维度下的人。

夹杂在日常琐事之中的我们时常漠视、遗忘了这些实则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议题,蒲英玮的创作试图在视觉表层之后企图将公众带入对现实的回应与批判。而这些创作也并非高屋建瓴,虚空无力的表达,对政治、历史等宏观叙述的持续性关注,直接源自艺术家自身的经历和直观经验。
2013年,蒲英玮前往法国求学,最初对法国生活的想象是可以随时逛逛卢浮宫,漫步塞纳河岸,享受着法式的浪漫生活。但是在法国的这五年,是法国社会极度不稳定的时期,游行、暴乱、恐怖袭击事件时常发生。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因发布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书《屈服》(Soumission)而引发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其中最为严重的一处袭击地点⸺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观众被劫持为人质, 导致近120人死亡。2018年“黄色背心运动”爆发时,抗议者的燃烧弹直接扔到了艺术家的楼下。 移民、身份、种族、政治、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因现实的动荡不安被激烈的提示出来,“这也使得我(蒲英玮),作为存在于西方社会结构下的另一种’少数群体’,天然地(或者说被迫地)遭遇了属于我的身份问题”。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波动和冲击对艺术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蒲英玮艺术创作传达的核心。

“我反对在某个既定权利下所形成的暴力,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会产生暴力,种族孤立或种族的崛起都会产生暴力,乃至自由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暴力,我反对这种抽象的暴力,我更反对那个抽象的权利。”蒲英玮言道。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它们像是一种隐身一样的存在,我们不会过多地感受到、思考到它们,但在某个时刻平静被击碎,你会发现它们从来没有走掉。不能一直停留在遭遇过后才知反抗的程度,Time,History,Why We Fight?的问题或许需要不间断的回应。正如,艺术家蒲英玮后续 的创作也将再次关注到一座由中国援建非洲的水利工程项目,虽然他对黑人问题的关注曾遭受过质疑,但是不正是如此才需要更多的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