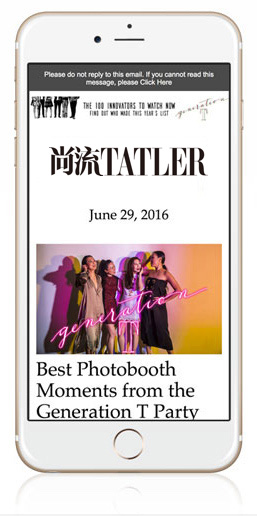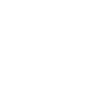郝景芳和王占黑,两个年纪轻轻就获得文学奖殊荣的女子,分别居住在北京与上海,一南一北,文风迥异。但她们都在创作之余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教育,用她们眼中的浪漫,扩展生命的维度。
郝景芳 X 王占黑 隔空对话
郝景芳
2017 Gen. T 新锐先锋
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得主 
SHANG XIA云气系列开襟白色毛衣
宝珀BLANCPAIN“月亮美人”腕表
从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到国际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得者,从天体物理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她既做宏观经济研究,也写科幻和现实题材小说,更致力于儿童公益和素质教育,创办了“童行学院”, 她总是以自己的选择和智慧,构建着人生的无限可能。

郝景芳作品《孤独深处》、《去远方》、《流浪 苍穹》,其中收录在《孤独深处》的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有光的人”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郝景芳对自己的规划,包括未来想学什么、做什么、该如何度过一生、如何安排时间,都有了自己的主意。郝景芳对于自主学习的能动性,致使她不需要反复做题,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方式将知识读懂。“读书给人思维带来的提高,是会长期显现的。”就这样,郝景芳无形中成为了被交口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
 大三时期的郝景芳
大三时期的郝景芳
而她自己心中对于“别人家的孩子”却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她称其为“有光的人”。“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去看那些在世界上取得很多成就的人,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从小就是自带光芒的。像爱因斯坦小时候就开始思考一些很深奥的问题,由于求知欲或者好奇心的驱使去做研究和发现,长大以后就变成了不起的人。我自己觉得自己只是在学校里成绩考得好一点,比起这种真正厉害的人物还差得远。”
 在腾讯WE大会上郝景芳分享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
在腾讯WE大会上郝景芳分享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
即便是在清华大学读物理专业期间,郝景芳也没有遗忘写作,书写是她早已养成的生活习惯。早期写小说,郝景芳特别注重氛围的空灵感。“当时的我希望自己写的小说本身是有飘逸的感觉或者比较灵动的地方,让人感觉出跟现实世界不一样,跟所熟悉的生活不一样,跟我们读到的文章也不一样。”后来随着个人的成长,她在小说中越来越重视人物和故事情节,关心人物的命运和内心,“因为经历多一些,看到的人也更多一点,会有那种为了某个人的生活难过的心情,这种心情会转化为对故事情节的重视,会开始想要写更多关于人世间的事情。”
 领英影响力大会的圆桌会议上,郝景芳以自己的人生感悟鼓励在座的新青年们永远要向前看,即便是现在非常艰辛,但未来会到达希望的地方
领英影响力大会的圆桌会议上,郝景芳以自己的人生感悟鼓励在座的新青年们永远要向前看,即便是现在非常艰辛,但未来会到达希望的地方
最近,她在写新的长篇小说,核心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其间她一直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丛林法则的相互争斗和拼杀之中,到底有没有纯粹的善意?郝景芳的写作是清醒、自由和孤独的,文学和科学构成了她文本的两个要素。对宇宙万物的了解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使她的写作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不缺现实层面的同理心。她用文字构建空间,让读者顺着她的文脉进入到一个广阔的时空里,从而感受到蓬勃生命的无限张力。
 郝景芳以Global Cultural Leader全球文化领袖的身份受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郝景芳以Global Cultural Leader全球文化领袖的身份受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郝景芳认为,时间才是我们生活真正的舞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热衷于扩大自己的空间,一旦有势力了我们占土地,一旦有钱了我们买房子,但不管你占了多大的地盘,一个人所能站的就是双脚这么大的地方。不管一个人有多厉害,最多也只能活百年。所以,怎样让自己的时间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这才是一个人生命意义的最重要的维度。”
尊重和自由,成就浪漫的生活
郝景芳每天几乎只睡四五个小时,却总是精力充沛。刚生完二胎,大宝刚满4岁,照看两个孩子近期占用了郝景芳生活的大部分精力,写作基本上都在碎片化的时间,而她于2017年创立的“童行学院”需要搭建更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内容框架,有很多社会活动需要参与。
 AKRIS 皮衣外套、皮裙
AKRIS 皮衣外套、皮裙
宝珀BLANCPAIN“月亮美人”腕表
她想要用公益实践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消解她在《北京折叠》中所描写的阶层差异,以注重思维方式的教育,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开拓另一种可能性。“好的公益必须给人赋能,不能只是送钱和物资。”郝景芳对“童行学院”的期待是没有施舍与被施舍,只有思想相互交流,互相尊重,“孩子们可以在‘童行学院’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各种方向的课程内容,让他们对于想要学的东西,想要走的人生方向,产生强大的自我驱动力,最终找到自己的内心之光。”
 参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的“一元营养包计划”公益项目的郝景芳,为贫困地区6-24个月的婴幼儿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营养
参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的“一元营养包计划”公益项目的郝景芳,为贫困地区6-24个月的婴幼儿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营养
从刚成立时的十多个人,发展至今40人的团队,成立“童行计划”后她的生活几乎没有停歇过。她在怀孕九个月的时候还在坚持给孩子写课程,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刚生完宝宝两周,她就开始做课程直播,陆续恢复工作。她最近录的一个文学音频课程是给孩子们讲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她尝试让孩子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小美人鱼的选择。“文学带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和馈赠,是在人生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我们能够真的尊重孩子的思考的时候,会获得更多的东西。”
 郝景芳带着她翻译的儿童绘本《追星星的人》来到上海童书展现场与小朋友面对面分享
郝景芳带着她翻译的儿童绘本《追星星的人》来到上海童书展现场与小朋友面对面分享
如今,尊重和自由,是郝景芳生活中重要的关键词,她和父母、先生和女儿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包容和默契,即使大女儿现在只有四岁,她也从不会强迫她接受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希望女儿像她小时候那样自由地成长。
 曾经荣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郝景芳,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名纯文学作家,她在高考填志愿时报了物理系,那是她觉得自己此生做过的最浪漫的选择。做天体物理的观测、研究黑洞和探索宇宙的奥秘,对她而言难得而珍贵。郝景芳对自己的生活也有着无数浪漫的想象,她想要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浪迹天涯的同时读书、写作,也许那将会是另一种浪漫。
曾经荣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郝景芳,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名纯文学作家,她在高考填志愿时报了物理系,那是她觉得自己此生做过的最浪漫的选择。做天体物理的观测、研究黑洞和探索宇宙的奥秘,对她而言难得而珍贵。郝景芳对自己的生活也有着无数浪漫的想象,她想要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浪迹天涯的同时读书、写作,也许那将会是另一种浪漫。
王占黑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
 MICHAEL KORS 粉色毛衣
MICHAEL KORS 粉色毛衣
宝珀BLANCPAIN“月亮美人”腕表
去年秋天,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王占黑和她的处女座《空响炮》同时进入了大众视野,评委们给她的颁奖词是:“90 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然而她却说,自己才写了两本书,不算“作家”,只是“作者”而已。
 王占黑的处女座《空响炮》
王占黑的处女座《空响炮》
在时光里安静漫游
拿奖之后,王占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各种媒体采访蜂拥而至。“要说庆祝的话,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周末,约几个好朋友去滨江西岸溜达了一晚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这也算是我平时最喜欢做的一个事情。”
 王占黑以旧社区为中心的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赢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王占黑以旧社区为中心的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赢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从最早在网络上写作,到去年开始出书, 走路一直是王占黑放松自己的方式,也是从家人长辈那儿沿袭下来的习惯。“我没有过采风的经验,总觉得不需要特意带着某种目的去做什么事或完成一个东西。因为做老师的关系, 工作范围比较单一,环境也比较狭窄,所以就会放自己到更大的城市空间,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然你就只面对的是你的同事、学生和你的教学内容。”
 ALBERTA FERRETTI钻饰高领黑色毛衣
ALBERTA FERRETTI钻饰高领黑色毛衣
宝珀BLANCPAIN“月亮美人”腕表
王占黑时常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对她来说,每条马路都可以走,很多地方都有看头,不同的街道有不同的人可以看。“就是乱走乱逛,有时候会拿手机拍一下,但不会特意去录音或者跟谁聊天,如果有一个自然的机会就聊,但不会刻意去创造机会。我一个小姑娘就这么看看,人家也不会赶我走。”王占黑说到这里,把下巴搁在台面上,完全是一个天真少女的神态,很难想象瘦瘦小小的她会书写老城区街头巷尾的人生。
 在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部做老师,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况且王占黑负责三个班的语文教学并身兼一个班的班主任,要对高三学生的升学负责。“本来我是一份主业,一份副业。现在是两份主业,所以就很累。手边第三本书写到暑假,因为开学就没再写了,打算寒假再继续。教书这份工作对于写作,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但的确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有想过是否要辞职,但作为班主任,想想还是得带这届学生毕业再说。”
在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部做老师,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况且王占黑负责三个班的语文教学并身兼一个班的班主任,要对高三学生的升学负责。“本来我是一份主业,一份副业。现在是两份主业,所以就很累。手边第三本书写到暑假,因为开学就没再写了,打算寒假再继续。教书这份工作对于写作,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但的确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有想过是否要辞职,但作为班主任,想想还是得带这届学生毕业再说。”
 从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王占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面临就业的问题,当时她完全没有信心用文字来养活自己。“可能大家对中文系的刻板印象就是做语文老师。也尝试过找其他工作,比如做公司职员,一年只有5天年假,好像不太适合我;在媒体行业做记者,写东西自由度不高,想想还是算了;后来发现在国际学校教书,可以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又有寒暑假,还挺好的。”
从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王占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面临就业的问题,当时她完全没有信心用文字来养活自己。“可能大家对中文系的刻板印象就是做语文老师。也尝试过找其他工作,比如做公司职员,一年只有5天年假,好像不太适合我;在媒体行业做记者,写东西自由度不高,想想还是算了;后来发现在国际学校教书,可以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又有寒暑假,还挺好的。”
 王占黑自知不能一心二用,所以不会同时开很多个文档进行创作,一定要等前一个写完了才能写下一个,实在写不下去了,就暂且搁置,“当你一头扎进去很深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全局,看不到自己所占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放松一下,换一个头脑,然后再回过头的时候,也许能有好的效果。”
王占黑自知不能一心二用,所以不会同时开很多个文档进行创作,一定要等前一个写完了才能写下一个,实在写不下去了,就暂且搁置,“当你一头扎进去很深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全局,看不到自己所占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放松一下,换一个头脑,然后再回过头的时候,也许能有好的效果。”
闯入文学界的人间观察者
王占黑不用微博,除了之前在豆瓣发表文章以外,几乎与社交媒体绝缘。但正是因为在豆瓣上小有名气,她得到前辈的引荐和帮助,出版了自己的作品。 出书之后,王占黑跑过几次书店的活动,做讲座和对谈。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表演的形式,虽然跟我谈话的人就坐在旁边,但要顾及台下的读者,倒不如大家围起来聊比较好。每次座谈都要坐在一个地方讲最起码两个小时,其实有点坐不住。”王占黑直言不讳,“当然,我从来不会觉得参与商业的活动,我就变了,在我看来都是人间体验,人间观察。而且一个人哪那么容易因为做了一些什么就改变了?难道不应该是我做了什么,就让那件事情发生改变么?总之我觉得没有理由在没有尝试的情况下就排斥什么。”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表演的形式,虽然跟我谈话的人就坐在旁边,但要顾及台下的读者,倒不如大家围起来聊比较好。每次座谈都要坐在一个地方讲最起码两个小时,其实有点坐不住。”王占黑直言不讳,“当然,我从来不会觉得参与商业的活动,我就变了,在我看来都是人间体验,人间观察。而且一个人哪那么容易因为做了一些什么就改变了?难道不应该是我做了什么,就让那件事情发生改变么?总之我觉得没有理由在没有尝试的情况下就排斥什么。”
 在读者见面会上,王占黑见过很年轻的中学生,也见过同龄人与退休的老者,年龄与背景跨度很大,她书中的人物同样如此,有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但她似乎更愿意用书写的方式来和他们产生关系。王占黑坦言,自己没有特别崇拜的老师,或者特别想成为的人,眼下作为一个老师,她觉得自己做得还算不错。
在读者见面会上,王占黑见过很年轻的中学生,也见过同龄人与退休的老者,年龄与背景跨度很大,她书中的人物同样如此,有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但她似乎更愿意用书写的方式来和他们产生关系。王占黑坦言,自己没有特别崇拜的老师,或者特别想成为的人,眼下作为一个老师,她觉得自己做得还算不错。
 “毕竟年轻,思维的活跃度是有的,所以能够讲的东西也会比较丰富和跳跃,跟学生会有一些连结。我发现其实在国际教育体系中母语的教学,不论是语言也好,文学也好,是有游刃度的,学校很在意老师的个体性。尽管我的工作还是要帮学生们应付考试、申请大学,但我还能够在受限的情况下去寻找最大的空间和自由。
“毕竟年轻,思维的活跃度是有的,所以能够讲的东西也会比较丰富和跳跃,跟学生会有一些连结。我发现其实在国际教育体系中母语的教学,不论是语言也好,文学也好,是有游刃度的,学校很在意老师的个体性。尽管我的工作还是要帮学生们应付考试、申请大学,但我还能够在受限的情况下去寻找最大的空间和自由。